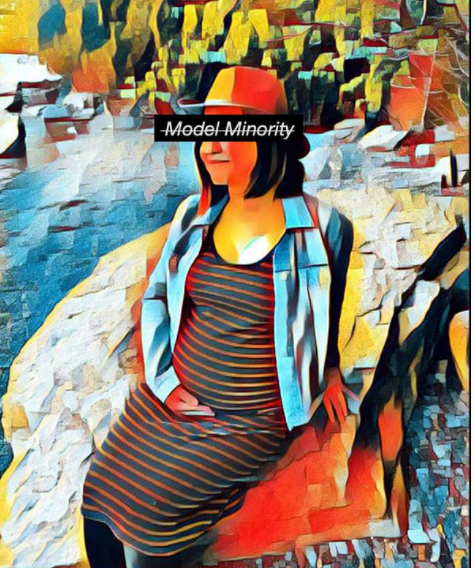*本文原载《多伦多星报》,作者为加拿大华人女子Yvonne S.。为保护隐私,撰稿人姓氏已被酌情隐去,本文将以Yvonne S.女士的第一人称进行叙述。
作为一名加拿大华人,我曾是主流社会口中“模范少数族裔”的一份子。聪明、好学、刻苦是我的“名片”,我的英语不带口音,我对别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威胁。也正因如此,我没怎么被种族歧视过。
我常常想着,只要我做得够好,种族歧视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模范少数族裔”的声誉会为我提供保护,加拿大主流社会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歧视我、骚扰我,白人也会把我当成他们中的一员。

所以,当我真正意识到,自己实际上被歧视了很久时,这一切都太晚了。“模范少数族裔”的诡话不仅提供不了保护,反而困住了我们——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种族歧视就这么发生在了我身上。近一年以来,不仅在大街上有对我谩骂的路人,工作场所中无尽的“微侵犯”(microagression)也时刻给我的心理和身体造成了双重打击。
一年前,我开始在一家中型慈善机构工作。公司里加上我一共有就两个少数族裔的雇员,其他的员工全是白人。头12个月,一切都看上去很好,我的工作也得到团队的认可,我也没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直到我原来的执行总监休了产假。
原来的总监修完产假之后直接就辞了职,公司没有花任何心思在招人上,反而直接从内部提拔了一个员工,这人上岗之前连正规的培训都没有——自此,整个公司的工作环境迅速恶化,原本高效的工作指令被无尽的权力斗争取代,新上任的领导也不知为何,对我和另一名少数族裔雇员充满敌意,专挑我俩“下手”。
英语里有个词组叫“pet to threat”,指的是少数族裔的女性在职场里首先被当“团宠”培养,然后等她的能力慢慢被培养起来,雇主就自然而然把她当成了威胁。
很不幸,我就被迫走上了这条职场PUA的道路。新领导上任后,开始一切都还好——我很感激她曾经在每个项目前都会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她也曾给过我很多成长的机会。但慢慢地,她开始压迫我,并对我展现出敌意。这个人开始在所有人面前严厉地指责我,还经常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里对我大喊大叫。吼我的原因也没有什么别的,只不过是一些拼写错误。
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偶尔会犯些拼写错误。就算是其他白人同事,他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有写错字的时候,但对其他人,这个老板也就简单发个邮件让他们改改,或者直接就文档的批注上改掉了。
就只有我和另一名少数族裔的女雇员会被被她突然贴脸,大声质问我们为什么犯这么幼稚的错误。我到现在还记得,一次有个客户的名字叫Sarah,我在做记录的时候写成了Sara(注:这两个名字的读音完全一样),然后就被她大喊了一顿。担心再被骚扰,我把所有名字全写了下来,然后贴在了桌子上。
拼错字被吼都只是小事——当这个领导知道我怀孕之后,事情就更糟了。
因为担心自己可能会流产,我在发现自己怀孕后并没有把这件事对任何同事说过。在我孕期第9周的某一天,我实在感觉不舒服,于是就想找她请个病假。领导拒绝了我,声称我非上班不可。情急之下,我不得不告诉她我怀孕了。
接下来,她就对我怀孕这个话题进行了无休无止地嘲讽。
几乎每天早上她都对我的孕吐颇有微词,声称不是所有孕妇都会晨吐,至少她就没有。但无奈孕吐还只是我众多反应中较轻的一种。她每天发表的负面评论让我甚至都不敢告诉她自己其他不舒服的地方——不然就只会迎来她更多的嘲讽。
我甚至得在她面前强行压住恶心,每次想吐的时候都得跑下楼——这样她就听不见了。
怀孕第11周,我还是很不舒服,这时领导让我吃点药。且不说吃不吃药是我自己的事,当我告诉她自己吃药没用之后,她反过来又怼我一句她的哪个朋友吃了药就没事了,一定是我的身体有病。

第13周,我每天还是吐得厉害。在我最不舒服的一天,我从楼下上来,筋疲力尽、满脸苍白的样子被她看见了。她又说我现在“不该吐了”,因为很多人在孕期满12周就不会吐了。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她还一直在我面前念叨这事。
在我所有的朋友里,我几乎是第一个结婚生孩子的,所以也没人告诉我如何用《安大略省人权保护法》和《加拿大人权法案》来争取自己作为孕妇的权利。到现在我才了解到,骚扰一个孕妇,那是要被重罚的。
而且对一个女人来说,怀孕应当是她最幸福的日子,可我却每天都活得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无休止的负面评论和骚扰对我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020年2月,我丈夫建议我要不要秀产假,或者干脆辞职算了,因为这个有毒的老板创造的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肯定不利于胎儿的发育。
妈妈被无休止地骚扰,孩子的发育受严重影响,没有哪个孕妇应该在这个慈善机构上班。
然后疫情就暴发了。除了对我怀孕无休止的风言冷语外,每次公司聊起“新冠”、“武汉”和“蝙蝠”这样的话题,我总是被领导点名,非得说点什么。我再也受不了每天在恐惧中工作,我更不愿意让未来的孩子和我一样经历这种恐惧,于是我辞了职。
离职那天,我忍不住在自家厨房里跳起舞来——我的孩子再也不用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成长。但我同时又非常生气:所有人都知道我被歧视,但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告诉我算了,不要惹麻烦。
我曾经也一度告诉自己算了,忍忍就过去了。直到另一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我。
乔治·佛洛依德“跪死”案发生之后,“黑命贵”运动席卷整个北美,办公室里所有人都跟疯了一样,在社交网站上转发着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文字,叫嚣着什么“我们要做更多”之类的话。
千里之外一个跟他们毫不相关的黑人让这帮人集体高潮,在办公室的我、怀着孕还要忍着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我怒不可遏,终于明白过来,是我的沉默和不作为导致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种族歧视。然后我正式向公司的高层发起了投诉,但结果却被打了回来——高层说经过讨论,并没有什么种族歧视存在。
我真的非常沮丧,因为在现在这个世界,种族主义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歧视我,他们甚至都不用像以前一样,叫我“中国佬”。而且就算有,我也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书面或者录音证据才行,不然,我的亲身经历对这帮人来说,就是谎言。
就算我想帮助公司制定反种族歧视的新政策,公司的高层甚至都不想理我。相反,我心底还升起一股莫名的愧疚感——来自社会的压力把我这种人定义为“麻烦制造者”,妄想让我对为自己发声感到耻辱。我甚至一度想说出“很抱歉我投诉了,给您添麻烦了”之类的话,但我又硬生生地咽了下去——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对的。
那个慈善公司悄无声息地开掉了这个女总监,有关她种族歧视的事公司一句话也没提,她在领英上的工作档案也看起来相当正常。
没人会知道她那恐怖的举止,而我以匿名方式撰文,恰恰就是害怕她的报复。我能做的,也只是分享我的经历,希望更多年轻、有理想的少数族裔女性能看到这篇文章,并学到你们无需容忍种族歧视。
“模范少数族裔”的诡话保护不了我们,能保护我们的只有法律。
文/程序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