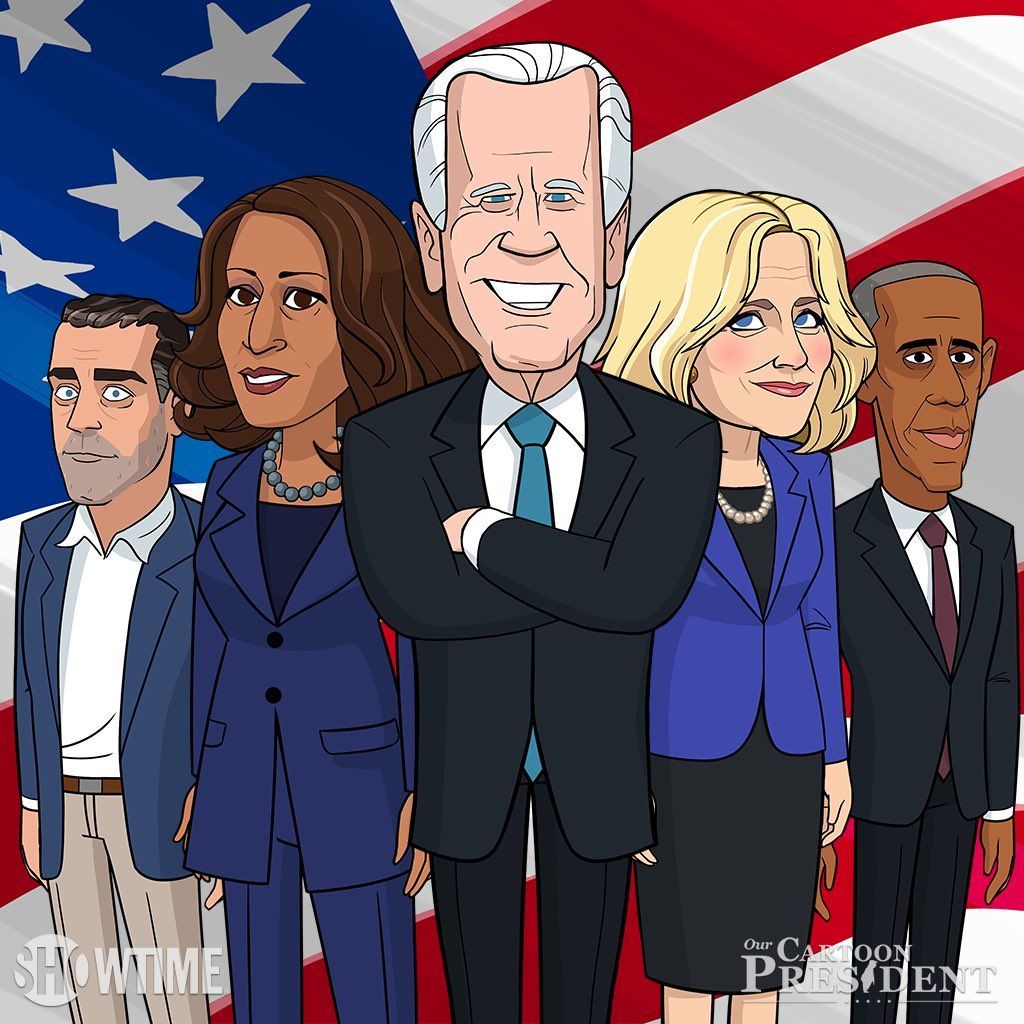围绕着总统大选的争议,美国的分裂和对立已经进入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这对美国强国地位的前途以及美国民主制度的命运,都有重要的影响。
拜登虽然在就职演说中呼吁“团结”,但进入白宫的具体操作后,团结的命题被党派的利益、或者是反特朗普主义的政治需要所垄断,在一周多的时间里,竟然发布了近数十个总统行政命令,远远超出了奥巴马和特朗普在白宫初期的总统行政命令数量的总和,引发了美国舆论关于拜登“是否独裁”的争议。而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则忙于2月8日即将开审的第二度特朗普弹劾案,重要的纾困计划以及内阁人事案件都受到了耽搁。

纵观拜登的总统行政命令内容,有的可以理解,有的根本无法理解。回到世界卫生组织,回到巴黎气候协定等决定,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且是拜登总统大选的重要承诺。在外交上,拜登团队对盟国广交朋友,修正特朗普的四处烽烟政策,也是可以理解的。德国外长在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交谈后,竟然发出感叹:太容易跟美国达成共识了,简直不可思议。当然,真的是那么容易达成共识吗?未必。当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共识就不值钱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率先向拜登示好,但拜登上台后的第一天,就把攸关加拿大经济命运的油管铺设计划给否定了。

在内政方面,许多总统行政命令就具有强烈的党派色彩乃至报复性质。拜登应该知道,特朗普有7400万选票,这是争取连任总统所获选票的历史最高,且特朗普基本盘的支持者比2016年大选多了近一千万。这说明了特朗普的一些政策是获得民众支持的。拜登既然说要做“全民总统”,就必须要考虑这些选民的立场。
但是,拜登采取的是“逢特必反”的方法,全面否定特朗普的政策。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回报前总统奥巴马对他的支持,他是帮奥巴马出气。同时,也是为了迁就民主党内的激进左右。但拜登很清楚,他如果不回到民主党的温和立场,而是被前总统奥巴马和党内激进左翼(比如以纽约州众议员欧加修AOC为首的少数族裔女性四人帮)牵着鼻子走,那么,特朗普或者特朗普主义的东山再起,是不可避免。

问题是,面临佩洛西和舒默(国会众参两院的多数党领袖)的不断分化,共和党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能否卷土重来,令人关注。
其实,反对建制派的特朗普保守主义,遭遇了两种势力的拉扯而引发争议,一是白人至上主义,一是极端右翼。试想一下,自己娶的老婆都是外国人,女婿是犹太人,这样的特朗普可能是白人至上主义吗?同样,具有亿万富翁商人身份的特朗普,也不可能是极端右翼。但是,由于特朗普没有政治敏感度和修养,大嘴巴乱说话,因此也被政治对手贴上了“白人至上主义”和“极端右翼”的标签,以至于共和党内形成了两派,一是支持特朗普,一是反对特朗普,前者需要特朗普的基本盘,后者认为只有切割特朗普,才能让共和党重生。

不过,2020选战也带来了一个吊诡现象: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没有特朗普的支持,共和党许多议员要落选;但是,一旦选举聚焦特朗普,共和党则输了总统大选和乔治亚州两名参议员决战。其实,保守主义的成败关键在于选民。随着郊区选民的左翼化,保守主义的人数劣势正在凸显,健康保守主义的命运其实在少数族裔选民手上。
加拿大面临的问题一样。如果联邦左翼政党四归一(即联邦自由党、新民主党、绿党、魁人政团),保守党要在渥太华执政几无可能。左翼力量很清楚,不能让少数族裔与保守主义挂钩,故而要把保守党打成右翼激进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反移民,在保守主义和少数族裔之间划下一道鸿沟。
因此,对加拿大保守党或者健康保守主义而言,如何让少数族裔,尤其是缺少印象基础的华人群体,纳入到加拿大主流保守主义的一部分(新鲜力量),而又不折损加拿大多元文化的特征,这就是加拿大、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如果保守力量高高在上,以为少数族裔或者华人只是可以利用的选票,而不是主流的一部分,那就是给极左翼的分化创造条件,并给白人至上主义和激进右翼的搅局提供缝隙,从而让保守主义走偏或者遭遇妖魔化。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