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在科罗拉多(Colorado)河大峡谷﹐我经历了令人心醉神驰的时刻。因为这不是梦﹐我显然是走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王国﹐置身于气势磅礴、苍润灵逸、绮丽多姿﹐堪称此景只应天上有的宫阙之中。
如同一切遥远的美都不可触摸一样﹐这默然无言地耸峙在人类灵性领域里的自然大杰作﹐也只能注视。
注视就是光——用生命之光注视人类生活的地球上不可再造的瑰丽殿堂。纵然它是那样的恢弘﹐好像超越了有限的世界门槛﹐延伸到人类目力不可逾越的领域。然而﹐倘若以我的目光为此端﹐以山体幽谷为彼端﹐那么在任何两点成一线之间﹐始终存在一条可让美色通过的直线。它是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充满魔魅诱惑的灵山秀谷画卷。
我立于高处﹐投眼于莽莽苍苍﹐冷峭神秘的天穹下﹐只见重重叠叠﹐延绵不尽矗立着时光老人用其无形的刻刀﹐把浓缩亿万年宇宙沧桑的伟巨巉岩﹐雕塑成无数峭尖如塔﹑叠层如阁﹑壁立如屏﹑孤峭如台﹑浑圆如柱……各种形态神采殊异的雄奇构件﹐然后一一耸立在大地的深处而直刺昊天的最高点﹐让阳光在它上面闪烁﹐天体围绕它旋转。它就是如此恢弘﹑庄严﹑瑰丽﹐以致我敢说世界上任何伟大建筑构件都无法与它媲美!
多少次﹐我把目光收近一点﹐顺着它斜落到腰肢的长发曲线﹐投放到凹凸嶙峋的悬崖峭壁的断层上。那斑驳﹑丰厚的断层竟然展示着亿万年海洋生物的生命化石。它又一次攫住了我原本就脆弱的心﹐使我面对着时光使生命演化为岩石﹐而岩石又凝聚了时光﹐失去了我原有的一点矜持﹐只感到自身之渺小﹐生命之短暂﹐从而获得了对待人生的一份明澈﹐一份自觉。
尤其令我由爱慕而赞叹﹑而膜拜的是﹕当我把目光由峭壁千仞移向深不可测的谷底﹐我恍若一下子沉落在似乎从开天劈地以来便已凝固的插天群峰的重重包围与裹挟之中﹔一下子感到好像有一种非人间的不可言喻的寂静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连头顶上飘逸的云﹐飒爽的风﹐崖壁石罅间每一朵花﹐稀疏草地上每一棵草所冒出来的也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寂静﹐甚至身边逶迤婉转低吟浅唱的科罗拉多河水彷佛此刻也喑哑了。幸而不久﹐我又恍然了悟﹕这种寂静便是峡谷特有的温厚。峡谷正是以自己的温厚承受一切浩淼与沉重﹐以自己的宽广接纳一切卑微﹑低下﹐以及不安的灵魂以归宿﹔而最终﹐又以自己的深邃与富丽﹐成就了山峦峡谷的巍峨与庄严。
大峡谷之美﹐存在于千古幽绝的静中﹗

二
清晨﹐当朝暾刚刚染红峡谷肩巅﹐而谷中升腾而起的云雾宛如一层细密的面纱﹑披巾﹑腰带遮掩着它朦胧的身影﹐我就感应到这彷佛是仙境里欲露还藏的琼岛。
瞧﹐那一团团﹑一缕缕飘逸着﹐浮动着的云雾﹐显然是带着峡谷酝酿了一夜的爱意袅娜而来吻着石罅中烂漫的山花﹐接着又飘忽而去舞弄悬崖间自己依恋的树梢。这景象不由在我心中引起一阵悸颤。只是那一刻我不能揭开丝丝缕缕披在峡谷身上的雾纱﹐无法看清它超凡脱俗的姿采。
只有当朝阳喷金﹐霞光万斛﹐为它气度高华地披上了彩衣——华丽的金﹑酡醉的红﹑葡萄的紫﹑鲜橙的黄……我才心响咚咚地发现这沿谷森列的峰峦﹐虽然只是那么随意的立着或坐着﹐有临地长立的﹐有绕水抱流的﹐有退坐山嵎的﹐有凝坐说古的﹐有凌空盘峙的﹐但整体看去错落有致﹐座座又各具神采﹕不是雄姿凛凛﹐纠纠生风﹐便是娉婷绰约﹐绮丽灵慧。它们围绕着天体旋转﹐不时变幻着绚烂的颜彩﹐一会儿粉红﹑橘红﹑赭红﹐等一阵子又变成黯红﹑酱红﹑紫红……
如果在阳光下这熠熠闪光的景色是一首抒情诗﹐那么﹐待到暮色悄然由青灰而暗紫地掩来之时﹐大峡谷又豁然成为苍茫中的一个童话了。
瞧﹐那一座座影影绰绰的庞然大物﹐似乎不是刺向苍穹的巍峨山峰﹐而是卧伏谷底的巨象﹑骆驼﹐或早已灭迹的洪荒时代的困兽。它们此刻全都屏息敛气﹐静悄悄地潜伏着﹑等待着。好像一俟某种信号划破夜空﹐它们就一齐冲杀出来。而到了主宰黑夜的王后月华珊珊而来﹐此刻的大峡谷又浸透着微醺﹐披上了更为庄重的色彩﹐越发显得空灵而深奥莫测了。
大峡谷之美﹐存在于瞬息万变的动中﹗

三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我告别大峡谷﹐在思念的长夜中陷入了狂想的痛苦。我蓦然想起十九世纪美国散文大师梭罗的一首诗。因为这首诗之于我﹐如果恕我更动几个字的话﹐我也许可以从中找到慰安﹐抚平莫名的感情向我袭来之痛苦……
这不是我的梦,
用于装饰一行诗;
我不能更接近上帝和天堂
甚于我之生活在大峡谷。
我是它的石罅飘拂而过的风;
我返璞归真
是它的水,它的沙,
而它的最深邃僻隐处
高高躺在我的思想中。
本文作者简介:
文野长弓,著名散文家,曾任加拿大大华笔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现为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委员,《华章》编委。著有散文集《席地而歌》、《竹的印痕》、《步履酪酊》等数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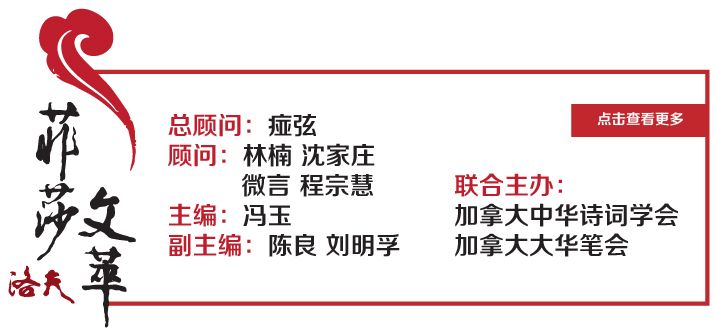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