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专用的那个小勺,舀一勺咖啡豆放进咖啡磨里。盖好盖子,慢慢地摇。摇啊摇,摇啊摇。隔着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日本枫树,在下午的阳光里,艳红的树叶鲜红鲜红的。
咖啡豆是我自己炒的。市场上有炒好了的咖啡豆;有的地方还有磨豆机,你选好的豆子当时就可以磨成粉。当然,袋包装的咖啡粉也有卖的。但我还是喜欢自己炒,自己磨。
还没煮呢,馨香的咖啡味已经从小磨里透出来了。有人说,喝咖啡的人真好,他们把香味给了别人,苦涩留给了自己。
这话似乎是在用喝咖啡去赞扬一种做人的境界。做人,我可远没达到这个境界,但是喝咖啡,我也许可以说到了一个境界了吧:豆子自己炒、自己磨,用的是手摇磨,煮咖啡的意式咖啡机、法式压杯、越式滴杯、玻璃滴漏瓶、土耳其煮壶等等,我都有。挺齐全的了吧?

而且,我喝咖啡不加奶、不加糖,就那么喝。这种喝法,英语称之为喝“黑咖啡”。黑咖啡有苦味,但我喜欢那苦味。
在国外时间长了,渐渐地喝起了咖啡。这也叫“近墨者黑”吧。
那年跟着旅游团到中国去。我们那一车五十多个团员,都是华人,来自加、美、澳,都是老侨民。休息时,导游说,这边有茶。习惯喝咖啡的,那边有咖啡。解散后一看,去喝咖啡的占了多半。
咖啡磨好了。我拿出了玻璃滴瓶。拿出过滤纸,捻出一张,在瓶里摆放好。
近墨者黑。可话是如此说,人在西人文化中,真的与西人融合在一起,真的不是件容易事。那时我移民加拿大七八年了,在卑诗大学教课也有两三年了。有一天,我让同学们带一些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到教室来,大家好一起交流一下,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交流。
大家带来的东西都挺有意思。有筷子,有中式烟袋,有中国毛笔,等等。有位女同学带来了一本画册。她打开给大家看。里面都是些中国历史照片。大家围上来,她一边翻,我一边给大家讲。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我的心情越来越不舒服起来。讲到那幅小脚女人的照片时,我说什么也讲不出话来了。大家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抬头看向我。那位女同学收起了画册。

我极力控制了一下心态。等我再看向学生们时,我发现那位女同学不在教室里了。我请大家自习,自己走出教室。在楼道里,看到了那位女生。在一个角落里她坐在椅子上,她在哭。
俗话说,儿不嫌母丑。这话其实没说清楚。它可以解读为“如果母确实丑,当儿的却并不能看出来”、“当儿的看出母丑时他并不会嫌其丑”、“当儿的不准嫌母丑”等等。究竟哪个解读对,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当时在我脑子里出现的是“当儿的容不得别人说其母丑!”
开水倒进了滴瓶。过了一会儿,褐黑色的咖啡滴滴答答地开始流出来了。滴滴答答地,滴到了滴漏瓶的下半部。
那位同学是在说我祖国丑吗?是在故意羞辱我吗?不是。但是,我的心里却分明升腾起一股压制不住的情感。它让我脸涨红,让我委屈,它让我说不出话,但又让我想喊出来。
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冷静下来了。在课堂上,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这时我意识到,今天的这一课其实也上给了我。
咖啡滴完了。我把咖啡倒进了杯子,一杯香浓的咖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不放糖,不放奶。我喝我的苦咖啡。
人们都认为喝咖啡是西方文化,但是,有多少人注意到了,咖啡其实原产于非洲?它来到了欧洲,在那里落脚、发展,后来喝咖啡在那里蔚然成风。咖啡,已经与欧洲人打成一片,已经融入了欧洲文化。
但是,欧洲本土仍然不出咖啡。咖啡,就连它的名字也仍然还是它原来的名字,“咖啡”是它本名的音译。它带着自己的本名,来到了世界各地,落了脚,成为了人们喜爱的东西。
本文作者简介:
习军,生活在温哥华。2017年成为加华笔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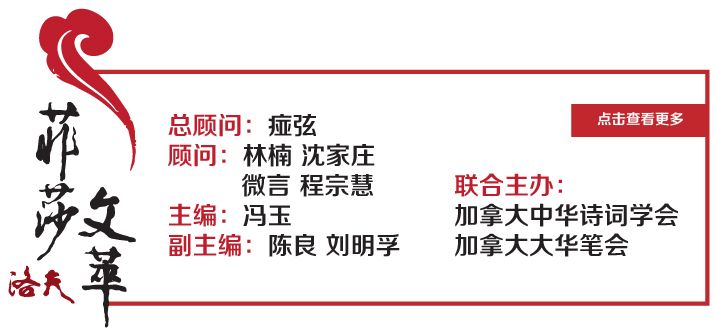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