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月儿圆,是中国传统的一家人团圆的日子,这个对于海外游子已经是一种奢望。
记得小时候每过中秋,母亲会自己烙些月饼。月饼里包的是红糖和花生或核桃。母亲把月饼包好后,往模子里一放,用手压实在了,翻过来,往案板上一磕,“啪”地一声脆响之后,一个漂亮的月饼就诞生了。在母亲双手的纷飞中,各种各样的月饼就排满了案板,有圆的:象征花好月圆;有动物形状的:象征生龙活虎。母亲烧了火,放一口大锅在上面,锅里不放水,架个铁篦子,把月饼放在上面烘烤,其实这已经是现代化的烤箱的雏形了。
记忆中有一年的中秋令人印象深刻,在石家庄做妇科医生的三爷爷回村里探亲。我们的小山村只有600口人。三爷爷此番回乡,除了和二位兄长及家人团聚,还邀请全村65岁以上的长者一起吃饭。全村大学生寥寥,三爷爷不仅考上了医学院,而且记忆力超人、过目不忘、口才极好,他一口气能滔滔不绝地讲两个小时,父亲听得津津有味儿。我也盼三爷爷回来,因为他会带城里的高级糖果。
我们一家人老老少少围坐在爷爷家的院子里,赏月拉家常。平时这一大家子人很少聚在一起的。三爷爷回来,大家都给三爷爷面子。爷爷弟兄三人。大爷爷是文盲,嘴巴像机关枪,想骂谁就骂谁;爷爷是校长,知书达理、和善豁达。老哥俩本来出入走同一个门,但因为性格不合,爷爷另开了另一个门,各走各的路。其实三爷爷跟爷爷从长相到性格都很像,属于英俊和气宇轩昂类的。三爷爷考上大学,到市里工作后,就和原配离了婚另娶了叫“李大夫”的。三爷爷和三奶奶互称“李大夫”、“段大夫”,“大夫”前冠以对方的姓,很是时髦。

那天晚上,月儿圆圆地挂在树梢,院子里像被柔和的丝绸抚摸着,我们一家人亲热地聊天。我当时上小学,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听大人说话。三爷爷的大儿子说起他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太奶奶,感慨万分,“有一次我问奶奶,‘奶奶,天塌下来怎么办?’奶奶举起她的拐杖指向天,‘我的孙子唉,你别怕,天塌下来奶奶用拐杖给你顶着!’”我对这句话记忆深刻,可能是觉得太奶奶这个答案充满了自信。现在想来,女人家能说出这样的话,太奶奶是何等豪迈!段家的男人有才,女人也是不同寻常的,比如我吃苦耐劳又聪慧的母亲。
如今,老人们已相继离世,三爷爷最小,却去世最早,因为肝癌;三奶奶不详,鲜有来往。爷爷次之,患了帕金森氏症;奶奶先于爷爷去世,宫颈癌。大爷爷寿命最长,我觉得和他的性格有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自然长寿;大奶奶是服毒自杀的,大爷爷摔了一跤,不能下地。大奶奶无儿无女,怕大爷爷的儿女指责她,寻了短见。真是惨烈!仨兄弟的婚姻,只有三爷爷是最幸福的,他勇敢地离了婚,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挚爱。爷爷的原配即是我的亲奶奶,在我父亲三岁时因为肺结核去世。爷爷后娶的妻子不识字,俩人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辈子没什么共同语言。大爷爷的原配是青霉素过敏去世的,她本来只是鼻子旁边长了个疙瘩。村里的医生连皮试都没做就给她打了青霉素,一针下去我大奶奶说口渴,水都没喝上就断了气。
时光飞逝,时空转换,转眼间我来美国已经21个春秋了。不在国内的环境里,过中秋的气氛越来越淡,我想起来的时候给父母打个电话,不像过春节时那样有规律,父母也不会怪罪。想来分离已成为常态。

但每每中秋节来临,看到圆圆的月亮挂在天边,心中不由得会升起一种伤感、一种想扑到母亲怀里的冲动。多么想,贴在母亲的胸口,倾诉分离的思念之苦、月明之夜的泪;多么想,坐在父亲的身旁,听他讲他高中住校时搞笑的事;多么想,听父母讲他们年轻时恋爱的故事:父母第一次见面,父亲坦白,“我穷的什么都没有”,母亲答,“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多么纯粹动人的爱情宣言!现在的相亲,命题离不开房子和车,让人啼笑皆非。
无边的思绪,像几场老电影,随着中秋节脚步的临近,被我穿了起来。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是那电影里的一个角色,我们在那里相见,互诉亲情和思念,互道珍重,期许最美好的未来。
作者简介
段莉洁,笔名若妖,在中国做过医生,在美国做艾滋病研究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写作17年,为文学城知名博主,发表文字100多万,为加拿大大华笔会会员,《加华文苑》散文部编委。曾在“我的父亲母亲”全球征文比赛中获佳作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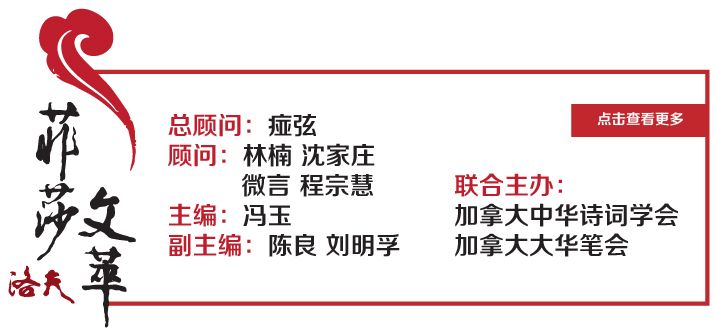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