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记住这一瞬间,仅仅为了它的平庸、实在,而妙不可言。那是早晨11点钟,我在故土新居的书房里,半躺着,读友人刚刚邮寄来的《文学江湖》——我至为景仰的文学大师王鼎钧先生四部回忆录的最后一部。读了20页,眼睛发涩,闭眼小休。位于第十五层的窗子,帘子微微卷舒,淡淡的云影在窗台停伫,又飘开,奶色的阳光又盘踞在枕头旁边。和风闪入。就在这一瞬,我的心涌上丰富无比的满足。人说遇到过于伟大或者强烈的美,恨不得马上抱着美死掉。我不想死,却难以找到一句话来总括此刻的感受。于是,被幸福憋得喘不过气来,只好独自微笑。终于想起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里的一篇回忆录,写他随表叔沈从文回老家湘西凤凰,作者道:“三月里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班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对了!此刻心情的最佳写照就是:哪儿也不想去了。

大洋彼岸住了近30年的家不想回去,天底下最秀丽的风景不想看,最炙手可热的人不想见,最脍炙人口的美食不想吃,天堂不想去,地狱不想浏览,只想维持这一瞬间,尽可能地久远。太美妙了,此刻!活了大半辈子,终于熬到,值了,熬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泪,这一瞬间都可以抵偿。
为了这一瞬间,拥有了生命的全部精华。第一是健康,我和妻子刚刚步行20分钟,到羽毛球馆,挥拍一个小时,大汗把全身痛痛快快地浇了一回又一回。论技术当然是末流之末,但我只要出汗。鲁迅有一篇强词夺理的杂文,讨论“文学与出汗”的因果,先指出:“‘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再来个归谬:“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鲁迅的逻辑大成问题,“出汗”属于生物性范畴,一如排泄,不存在阶级属性。我出的汗,香臭毋论,带来淋漓快感是没有疑问的。揩着源源涌出的汗时,自我感觉良好之极。全身还听从脑子的调遣,轻快自如,已在眉睫的老境并无威胁力。当然,好体魄是易碎品,在球场摔个跤或者某个脏器造反,我就马上被踢进病残族。然而此刻,我尽可及时行乐,快乐。洗个淋浴,穿一袭在四季偏冷、几乎从未出过爽快大汗的旧金山难得上身的纯棉质薄春衫,那才叫舒服。
第二,我似乎赢得了“看”的起码资本。我素所景仰的文学大家王鼎钧先生,从来都在兴致勃勃地看人,“给我更多的人看!”“一个写文章的人,还得感谢芸芸众生,感谢他遇见,看到的人,有人得意忘形给他看,有人老谋深算给他看,有人悬崖勒马给他看,有人赴汤蹈火给他看,有人高风亮节给他,有人蝇营狗苟给他看,有人爱给他看,有人死给他看。这一切人成全了他这个作家。”《文学江湖》予我的阅读快感是双重的,却远胜于商场“买一送一”的优惠。它展开广阔的时代,深层的人生同时,敞开伟大作家心的宇宙。我绝不敢和大师攀比,我唯一可自傲的资本,就是拥有初步地、肤浅地观照人生的眼睛,虽严重老花,小而被皱纹重重围困,毫无看头,但凭“看”来自娱,自省,进而将之化入速朽的文字,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这般陶醉在自我之中,哪里也不想去,倒退回到负重的中年时段、豪迈的青年时段,并不乐意;因为不甘愿舍弃岁月所赋予的淡定和悠远的心境。这种宁静,一辈子唯如今才有长久拥有,只有进入情欲消减近零度的晚年,才逐渐获致。当然,我也不想快马加鞭地老到拄杖,老到单靠为后辈写序过活,此刻恰到好处,有实行的计划和贯彻的能力。
这一瞬何其可恋!有这10秒钟,整个人生均算圆满。当人当了超过60年之后,粗略回想,可以和这一瞬间比美的,有多少次?23岁那年,在乡村当民办教师,星期六下午,学生和老师都差不多回家去了,我和家长学校附近的几个女学生一起打排球,我扣球,一位胖乎乎,从来不知道忧愁为何物的女孩子用双手垫球,我跃起,凌空狠命扣下球,她呲着牙,奋勇挡回,随即拧着手腕雪雪呼痛。那一瞬我也是这般快乐的。60岁那年的夏天,中午邮递员送来一个以胶带缠了许多层的公文袋,不耐烦一层层地剥,用剪刀剪个大口子,把书拔出来,那是大开本的《刘荒田美国笔记》,我爱抚着奶白色封面上的蝴蝶剪纸,“那种温软的感觉,像母亲的手掌抚摩你微微发烫的前额”(引自《文学江湖》),那天是2008年7月5号,28周年前的今天,我通过旧金山机场的移民海关,进入另一半人生,头顶上,是坦荡荡地、诡异地蓝着的异国天空。如果好事者非要给这秘密的快乐归类,我想起从前河北人的“四大快活”:坐牛车走沙地,穿大鞋,放响屁,往丈人家去。第一条可能取其稳当,第二条莫名其妙,兴许是宽松的舒服感,第四条指的是受优待,吃香喝辣,受丈母娘的宠爱。这三条都不切题,只好归入“发响屁”,这发泄是隐秘的(在稠人广众放要挨骂吃卫生眼珠),痛快的,且带点恶作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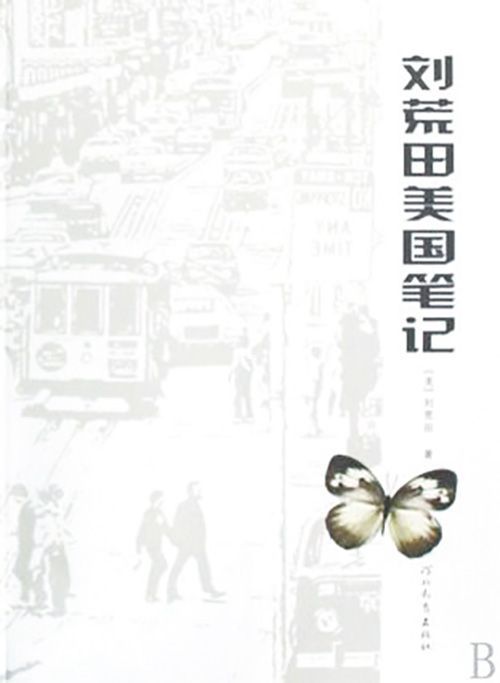
不过我最看重的,是这一瞬间的快乐,不需要任何工具,如钱,如醇酒美人,如清风明月。差不多一空依凭,只有大师的奇书,以及一个妻子刚刚买来、据说有催眠功用的枕头,里头的填充物是什么草什么藤云,好在没有中药味。妻子早早上街去了,这位热衷购物的主妇,一两个小时后将回家,一进门,便把大袋小包的搁在地上,夸张地叫累死了。对了,这就是我快乐的第三个理由:对人生作出预测的把握。日常生活的把握与写作上灵感的无从把握交织着。
归根到底,这瞬间的快乐来自:安卧的处所,位于我寄放晚年的故国。
作者简介
刘荒田,著名散文家。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移居美国旧金山,边打工边笔耕。2011年退休以后,开始在中美两国轮流居住。已出版散文随笔集37种。2009年以《刘荒田美国笔记》一书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所颁“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2011年,以散文《一起老去是如此美妙》获新疆“爱情亲情散文大赛”第一名。获《山东文学》杂志2015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第一名)。小品文集《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入围2019年“花地文学榜”年度散文。2017和2018年两年均进入三大文摘杂志《读者》、《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最受欢迎的报纸作者”前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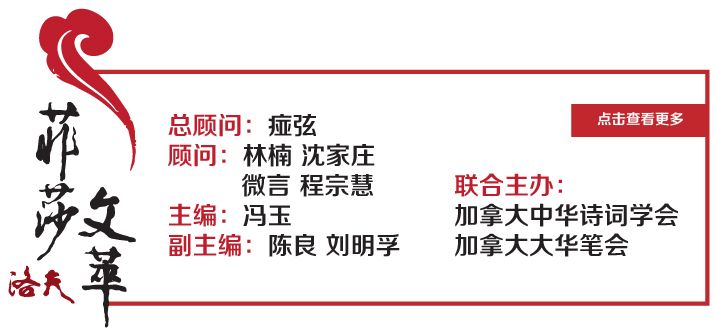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