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活着不能没有迷恋,迷恋是一种沉醉,迷恋是一种向往。然而,生命中大多的迷恋却总是想而不能得。
十年了,我在心底里轻轻怀想的竟是那“一缕茶烟”,黄昏的午后,阵雨初歇,瓦檐青苔,草色遥看,这时候,邀来相知相惜的友人,烧一壶上等的茶,青瓷的小碗,执在手中,放下红尘中所有的担当,只看云淡风清,只听笑语欢歌。融在清水里的茶不必多浓多醇,要的是那一刻远离生命之重的悠然,那一缕淡淡的茶烟袅袅升起的“闲”。可是,这样小小的一个迷恋,十年的岁月里竟无从实现。

早年因为读鲁迅的而走近了周作人,鲁迅先生是把喝咖啡的时间用来“战斗”,而同住在八道湾一个屋檐下的作人兄弟则终生沉湎于“生活艺术”的享受。最记得作人先生在他《雨天的书》里特别写“喝茶”:以他的感觉,“茶道”的意义是“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恒”。他老先生推崇的“茶”,是真正的“清茶”,“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要的是体味自然的“古风”。他那段最有名的话是“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先说“清泉绿茶”,那“清泉”就不可得。如今我们饮用的水,已不知走过多少人造的管道,哪里还会存有大自然山涧涌泉的清香?想当年《红楼梦》里的妙玉还能封存一罐洁白甘甜的雪水留给宝哥哥,我们的当代人在追赶车轮滚滚的途中只恨不得牛饮一罐“可口”的可乐立马气灌丹田。再说那“瓦屋纸窗”,如今的“瓦”也早已不是从前那青灰的真“瓦”,化学的材料已全然失去了厚实清冽的古朴。“纸窗”就更加无影,空调的室内几乎与四季隔绝,省心的建筑商只盼望将那“窗”干脆就掠去。至于“素雅的陶瓷茶具”倒是不难寻,难的是“同二、三人共饮”。这“共饮”的人,不为“交情”,不为“索求”,只为能共享这生命里的一段智慧时光,兰芳蕙心,同为性情中人,这不可谓不难。即便生命中寻得有,又须共“得半日之闲”,就更加一个难。古人曰:“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还要“二、三人”!

愈是不可得,就愈是勾起我无限的向往和迷恋。尤其是一想那“半日的闲”,竟能“抵十年的尘梦”,其中的蕴积是何等的深厚?终年跋涉在红尘的浮华之中,多么想啜饮一杯自然的“清茶”让自己回归身心;岁月网在疲惫的家居城堡,多么想借这“一缕茶烟”,让琐碎芜杂的心凌波超越。面对相知相惜的友人,说说自己的心事,会心的一笑,释去平生一蓑烟雨,遥叹一汪沧海。或者,就说说那李白、杜甫当年西望的长安,扯远了,再絮絮司汤达、巴尔扎克笔下醉眼神迷的巴黎。有道是,春的花,秋的月,夏的荫,冬的风,生命里因为有“茶”才看见了自己,若再有了对影“共饮”的喝茶人,谙哑的岁月才有了歌唱。

然而,对于这样的“茶梦”,永远也只是怀想。每日的清晨,残梦中惊醒,日竿的逼照容不得我心驰八荒,浑沌的脑海须借着一杯浓浓的咖啡方能振作,日程的紧迫又哪里能允我悠然等待那一缕茶烟的沉落?待到午后,终于有了片刻的“闲”,遂想起早先在伦敦街头看见的喝茶读小报的英人,豁然给自己斟一杯热滚的清茶,那淡淡的茶烟确是从手中袅袅升起,心却不能静,窗外红尘依然,不能诉说,也无从倾听,空寞的世界只有从手中沙漏般流淌,敲打着我“独饮”的哀伤。再到黄昏的傍晚,竟是一日忙碌的高潮,仿佛要给自己一个圆满的交代。终于到尘埃落定,夜深人静,更是不能饮茶,生来多梦,茶的多情只会是加剧当晚乱梦的消耗。那一刻,也只有“酒”微醺,能舒解疲惫的心,意志消融,恍恍然沉入那“杨柳岸,晓风残月”。
说到咖啡、茶和酒,唯独就痴心爱“茶”。咖啡让人沉迷于虚幻,酒能让人冲动地忘我,手中的“茶”却是容你慢慢地怀想。那股淡淡的香醇从心底里悄然溢上来,以它微含的苦,慰籍着生命的无奈,抚平着人世的憾缺,呼唤着与你共饮的人。
本文作者简介
陈瑞琳,美国著名华裔作家、评论家。曾任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现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兼任国内多所大学特聘教授。多年致力于散文创作及文学评论,多次荣获海内外文学创作及评论界大奖,被誉为当代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研究的开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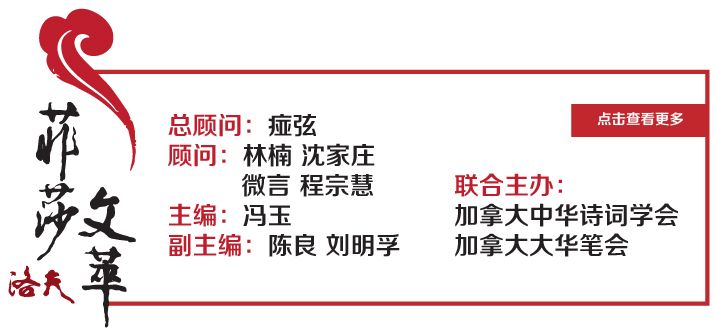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