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班的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到园子里四处看看。园子不是很精致整洁的花园,也不是颇费匠心的人工园林,如日本式的、苏杭式的小亭台、小流水……我的园子甚至可以说有点杂乱,我称之为“凌乱美”,这表现在随处乱长的荒草杂花上。不经意间,不知何时就冒出一支亭亭的箭兰、一把粗壮的马蹄莲,或一些稀奇古怪的不知名的植物。大地的慷慨总是给我许多意外的惊喜。而一个朋友,将吃过的枣核随手扔入园中,说不定哪天就长出一棵枣树来。
一场雨后,冒出水汪汪一片绿色的汲汲草来。而这种草,令我想到童年。那时我与小伙伴们在公园里采摘过这种草吃,印象中是酸酸的。除了汲汲草,我吃过的草还有兔儿草、车前草、折耳根,还有家乡山坡上一串串一骨碌新鲜的槐花,就这样摘掉芯放入口中,好清新、好滋润的口感,至今口齿留香。也许是我属兔的天性,至今看到长得青翠茂盛的草,我就好喜欢,喜欢得有想吃的冲动。
时值秋天,应该是草木凋零的季节,可是果树们,居然在这时候开花了。前不久才摘掉苹果树上残存的果子,可现在却满树开出了粉色的花朵,那么毫无顾忌地张扬着自己的美丽。而梨树则要羞涩许多,只在叶间淡淡地开出几朵纯白的小花来。而橙子树、枇杷树则好像真是忘记了季节,满树的花骨朵,像在迎接春天,而前方,等着的却是冬呢。
从我书桌前的窗前望去,一栅栏的牵牛花有好几米长,它们甚至攀援到左边高高的树上,与树上的红果子交相辉映。邻居园里高大的柠檬树四季挂果,无人采摘,任其边掉边结,循环往复。儿子曾告诉我,掉在地上的果实,原本就是树木的肥料,是我们人类改变了这种生物链,吃掉了原本该树吃的果实。

院子的左边,高大茂盛的树木们,遮断了与外界的视觉联系,令我仿佛在青城山下。而右边巨大的针叶松树下,是我们的书房,故名“松下堂”。松下堂指的是松树下这一方小小的庭院,院中之院,而真正的书房“无闻居”,就在小院中。无闻居里悬有一副对联:“居称无闻,家有尔雅”。
晚上,我在露台赏月,窥见有人在纱窗内做饭。见窗外有人影晃动,他明知故问:“谁在外面?”答曰:“报答你的桃花仙子。”他答:“还不如田螺姑娘,可以帮我做饭。”可见,浪漫与现实相较,人更注重后者。
坐在午后的摇椅上,蓝天白云,天空澄澈得纤尘不染,鸟儿的叽喳成歌墟。视野里的那几蓬翠竹,已长得很茂密了。可当初是那么稀稀落落的几株,且是好几处聚来的。可怜那个书生,为了砌这个养竹子的花台,被水泥将一只手腐蚀得斑驳粗糙,因为我在他耳朵边念叨:“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没有市井的喧嚣热闹,只有虫声、鸟声、果实坠地声……但也免不了烦心事:前些日子,有一只浣熊在我们的地下室安了家。这个不请自来,不交房租的霸道房客,不仅唏唏嗦嗦地半夜弄出声响,让我们不得安宁,它还袭击园子里的小鸟和松鼠。这个昼伏夜出像只大猫的家伙,有时在园子里闲庭信步,它看上去真得很漂亮,有着光滑柔亮的皮毛,勇猛壮实的体态,大而贼亮的眼睛。有天晚上,我们堵住了它进出的通道,但第二天,发现它奋力拆开了另一处木板,开辟了新的通道。雨后的露台上,全是它美丽的梅花蹄印。清晨它从露台下出来,正好与我打了一个照面,那一双漂亮的眼睛里,不仅没有恐惧,反而有一种挑衅。我惊讶于它何来那么大的力量拆开木板,却原来它已在里面生儿育女。母爱的力量,原来在野兽中也是这样强大。
我常常想,这种与大自然的树木花草为邻的、没有太多物质需求的简单生活,与现代生活的火热是多么格格不入。但我喜欢这种简单,欣赏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她是敏锐的自然观察者,在自己的花园中,几乎足不出户,一生都在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而那些诗篇,正是她的喃喃私语,对美的赞颂或秋的忧思,均记载了她灵魂动人的永恒瞬间:
“如果你能在秋天到来,我会把夏季拂掉。
半含轻蔑,半含微笑,像主妇把苍蝇赶跑。
假如一年后能看到你,我将把月份绕成团,
分别放在不同的抽屉,等待那些时间来到。
……
但是,现在毫无所知,你我何时才能相聚,
这像毒蜂一样把我螫伤,却未见它的毒刺。
作者简介
尔雅,本名张晓敏。加华笔会会员、海外华文女作协会员,北美中文作协会员。著有《青衣江的女儿》,《阳光如赊》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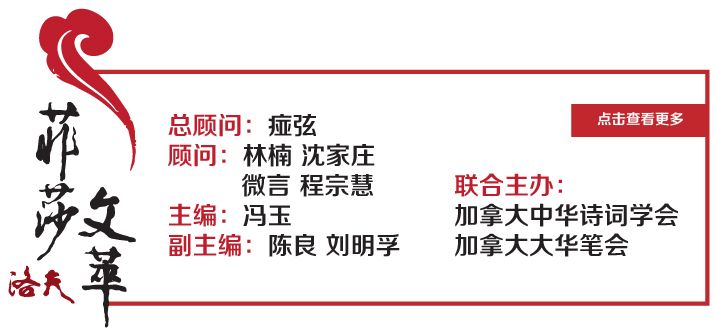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