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对秋天有偏见,因为不知谁用“秋风瑟瑟”来形容秋天,对我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直到去年的秋天我才解除了对秋的误会。我和先生去逛了明大的植物园,被秋的美深深震撼。秋天的美是浓郁而艳丽的,满树的橘黄、火红,漫天漫地地连成一片,象一团烧起来的秋火。
今秋,我想起了去世23年的爷爷。“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成长的路上有三次里程碑式的收获季节:离家上重点初中、上重点高中和大学。每次收获季节——秋季开学都是爷爷主动送我去的。爷爷一向以我为傲。小学时候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数一数二,爷爷主动提出掏钱供我上学。
我的初中是一所重点初中,我本应去另一所初中的。但爷爷想让我去这个重点初中,爷爷认识那儿的校长,让我通过考试进了那所中学。开学时,爷爷骑车送我。当时的爷爷66岁,二十多里地的路程,爷爷在后座上给我带的被子脸盆,间或护送我,因为我那时骑车技术实在不高,不小心会骑到地沟里去。

我上了我们市重点高中,69岁的爷爷又送我去上高中,那时改为坐汽车了,但是也要到离家十几里地的乡里去坐车。记得爷爷一次给了我60元,但我就很快就花光了。到了城里,东西自然贵些,而且可能物价已经飞涨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为我的“浪费”心里难过了好一阵子。
我考入省里的医学院后,73岁的爷爷又主动请缨送我去,爷爷当时已经患上了帕金森氏症,走路都颤巍巍的。坐在火车上,我当时心里有个可笑的想法:是爷爷去送我,还是我照顾爷爷?但很快又自我检讨:爷爷带病送我去上学,我怎么可以有那种残忍的想法?一路上我悉心照顾着爷爷。到了省城,爷爷送我的光荣任务结束了,在大伯家住了几日就回老家去了。我第一次到省城,投入了一片新天地,只觉得把爷爷交给了大伯就完成了任务,颤巍巍的爷爷回家时,我也没有去车站送。长大懂事后,不免唏嘘。
爷爷对我恩重如山,我除了每次回家跟他告别时舍不得他、抱住他哭泣以外,其余的什么都没有做,我理所当然地以为伺候他老人家是我父母的责任。我在大学里是个好学生,潇洒地生活着,在舞池里尽情地旋转着;在医院里是一个好大夫,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每一个病人;再后来嫁人,做一个好妻子,开启新婚生活。我总是那么忙。结婚第一年后带他的孙女婿去看爷爷,也似乎是礼节性的,因为结婚第一年后要去长辈家拜访。当时父母已经搬到镇上去办医院,从镇上到老家还有二十几里地,交通似乎成了我和爷爷之间的障碍。我婚后第三年爷爷去世。

接到爷爷去世的消息,我赶回老家,我亲爱的爷爷已经躺在漆黑的棺材里。爷爷的面容很安详和蔼,就象他生前一样。他先前做老师、校长,退休后继承了我太爷爷祖传的正骨按摩,开始治病救人。他英俊、为人和善、因为聪慧而技术高超,他对病人和家属客客气气,我从来没有看到爷爷发过怒。他虽面容和蔼,但气宇轩昂,自带一种威严。我小时候有些怕他,但又馋病人送给他的点心,隔三岔五问他要点心吃。不过,但又不想说自己想吃,于是编造理由,理由多是我姥姥过生日,爷爷笑着问我,“你姥姥一年过几个生日啊?”我被爷爷看穿,无言以对,怯怯地看着他,他还是给我这个“不会撒谎的老实蛋”吃了点心。
爷爷出殡的前一晚需要亲人守夜,我对这规矩似懂非懂,又觉得是封建迷信,还不如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好好哭他。当时也没人要求我守夜,我和家人亲戚在爷爷的大炕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醒来去爷爷棺材停放处,听到姑姑正在大声说,“白供她上学了,都不给她爷爷守夜!”我知道她是在排我的不是,心里有些惭愧。她看我走来,噤了声。
其实现在想来,年轻时不懂事,没去照顾爷爷,而当我懂事的时候爷爷已经长眠于地下。正值秋日,愿秋叶捎去我对爷爷的忏悔和思念。
作者简介
段莉洁,笔名若妖,在美国做艾滋病研究,文学城知名博主,发表文字100多万。加华笔会会员,《加华文苑》散文部编委。曾在“我的父亲母亲”全球征文比赛中获佳作奖,在天鹅杯“中秋”全球有奖征文中获传统文化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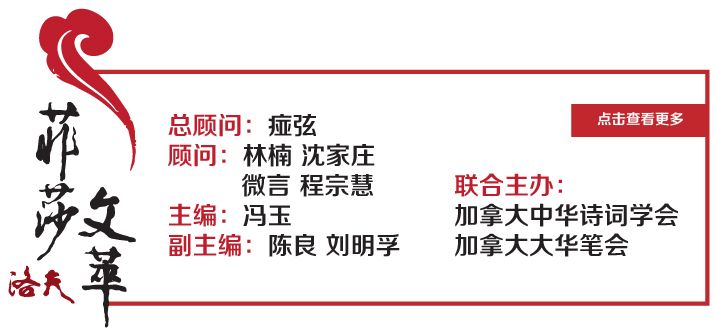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