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华秋实,流丹烁金,是美之源,歌之泉。无论三月的樱还是十月的枫,美如画,灿若霞,引代代文人墨客为之击节感叹。而在温哥华,不能不赞美秋枫,但这美要从春天说起。
“你看看这个。"立春那天早晨,遛早儿回来的妻递给我一片葱绿色的枫叶。“知道你喜欢枫叶,特地给你摘了一片绿色的。”
收拾书房时,她看到我夹在一本画册中的枫叶,这是十年前早晨遛狗时的副产品。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枫叶早已风干,叶面也起了皱纹,色彩暗淡,但依然能想象得出当年这些枫之骄子叱咤风云的壮丽灿烂。
看惯了国旗上的红叶,眼前这片绿色的枫叶却有些异样。近乎等边三角形的绿枫叶,三个叶角向左中右伸展,每个叶角的边缘都有一些微细的齿角,给叶面油然增添了层次和妩媚。细察,叶脉清晰,纹理毕现,犹如人的经络血管,主脉、分脉、末梢逐次延伸,直至叶子的边缘。

第一次看到加拿大枫叶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在安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白求恩故居。时值仲秋,小镇上冷清肃杀,阒无一人。走出故居小楼,望着一地红彤彤的枫叶,似地毯,又宛若仙境,有种异样的美。“能离开童话般的家园去支援中国抗日,我们将永远纪念白求恩大夫!”我对故居管理员金发碧眼的漂亮姑娘说。她注视着我,眼里充满了感动。于是,她捡了几片火红的枫叶,留下娟秀的花体签名,腊封好送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从此我知道了加拿大的国树是枫树。每每看到醒目的白底红叶国旗,便会想起那片腊封的红叶,那栋红枫映照下的豆青色两层小楼,想起白求恩灿烂壮美的一生。
温哥华有150余种枫树,有外来品种,也有本地土生。各式各样的枫树装饰了小区的街道、公园、操场,甚至通衢大道两旁也常有枫树侍立护卫。这些枫树高矮不一,有的三十余米,有的十米左右;叶片迥异,有圆润若佛掌、丰腴似环肥的钝三角形,有苗条修长的六角形,还有细身掐腰如燕瘦的多角形,但最多的还是五角形;色差变化大,春夏带来浓郁的绿荫,深秋初冬则以酣畅的色阶装点整个城市。
最常见的藤枫(Vine maple),7-9个叶角簇拥成圆形,夏天的酸橙绿秋天变成芥末黄和深红色。道格拉斯枫(Douglas Maple)也是本地常见的枫树。叶子有3-5个叶瓣,夏天的时候树叶是深绿色,秋天的时候会转成橙红色。与这两种矮小的身躯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大叶枫(Big-leaf Maple)。在空旷的地方,常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或一排排近三十米开外的巨人枫矗立。其硕大无比的叶片足有轻罗小扇般大小,五个深绿色的叶瓣秋天会变成明黄色,无比清新,醒目怡神。与之成为孪生兄弟的是外来品种梧桐枫(Sycamore Maple)。只是其叶子的正面是深绿色,反面显灰白和紫色,秋天也会转成黄色。

我们小区里则生长着另外两种枫树。不知其名,但相依为伴,如影随形;个性迥异,反差鲜明。
街道一侧的树皮呈深灰色,一道一道的竖纹像极了沧桑岁月的留痕。年龄稍大些的间或出现一两个瘢痕,犹如老人斑,显示了年轮的内涵,记载了深厚的阅历。姑且称之为竖纹枫吧。而另一侧的则树皮灰白,似白桦,如白杨,白皙细腻,几无雀斑,十分平展,尽展青春芳华。权且称之为白肤枫。
大约园林局有意为之,使两者毗邻,相伴为侣,相映成趣。每天早晨带着小狗散步,扑入眼帘的就是这两位相得益彰的伴侣。
竖纹枫树冠高若浮屠叠嶂的松塔,矮似蜂巢密实的松果,但枝叶都很紧致,层层叠叠,密密匝匝,厚厚实实,给人以敦实厚重之感。每一枝条都挑着一串串厚实的叶子,叶片下是一砣砣密集的豆绿色枫荚。约两寸长的枫荚犹如颌首的蜻蜓,薄翼舒展,似蝶飞舞,若雁展翅;落在地面时一片片围绕着母体,像极了一步一徘徊南徙的大雁,又似归去来兮的飞镖,恋恋不舍,不忍离去。白肤枫的树冠则犹如青丝高挽的妙龄少女,风鬟雾鬓,蓬松高冷,却又不失匀称和妩媚;又似睡眼惺忪的少妇,叶片轻舒,枝丫张扬,如虬龙走凤,尽展绰约。但不似竖纹枫,白肤枫没有枫荚,无牵无挂,倒也利索。
说到叶子,竖纹枫的呈五角,微细的齿角环绕着叶瓣,丰满妙曼,赏心悦目。而白肤枫的叶片只有三个角瓣,也无齿角的装饰,显得有些呆板单调。叶片呈巾字状,只是中间的一道饱蘸翰墨,一竖下来冲墨洇散,浸润了两侧的叶瓣,使叶片显得有些慵懒富态。
其实,两者最大的差异在其性格和行事风格。
春和景明,碧空如洗。两行枫树在清晨小鸟的啁啾声中苏醒,静思默想。枝丫纹丝不动,在空中静静地倾听天籁之声。竖纹枫枝丫低垂含蓄,宁静中显出沉稳、内敛和厚重;白肤枫则姿态跃如,枝丫伸展,叶片张扬,似乎随时都要拥抱这个世界。
朗朗夏日,一片乌云飘来,一阵气流过后,相依为邻的两伙伴便闻风起舞。竖纹枫的枝叶飒飒作响,在维度空间里摇曳,随着整棵树一起律动,矜持而稳重,颇有些绅士风度。而白肤枫呢,却有些不甘寂寞,急不可耐地摆动起腰肢,枝叶尤其夸张,每一枝每一片都在晃动,生怕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却略显一丝轻佻和浮浪。
不期而至的狂风沛雨则将两者的性格展现无遗。哗哗的声律中,似金属片在叠打,发出啪啪的声音。一支支、一串串、一片片的叶片簇拥成了一道道枫涛,一波接一波地涌将过来,整棵树犹如一片厚重的海,上下翻滚欢唱,迎接风雨的洗礼。而身畔的白肤枫则似按捺不住的桑巴女郎,虬龙般的枝叶金蛇狂舞,上下狂野抖动,左右恣意摇摆,终于有机会发泄情感,释放囚禁已久的欲望和激情。
“立秋了,给你这片枫叶。”一天早上,妻从外面拿回一片五角的枫叶。中间的主动叶脉已呈现紫红色,渲染得支叶脉也都变红,似厚积薄发时的血脉贲张,喷薄欲出。
“枫醉未到清醒时,情落人间恨无缘。”不由地想起了北京的香山红叶。香炉峰没有此地如此热烈浪漫多彩的枫叶,红叶也就是五角枫、三角枫,主角当属黄栌。但当红黄交织的柿树、李树、鸡爪槭、银杏等在黄栌的带领下将满山满谷装点起来,却有一种无可言传的隽永秀美。故乡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那绵长的流韵和情意,只能是有家不能回的海外游子方能意会、理解和欣赏。

说话间,寒露已至,枫叶开始了嬗变,将贮存了一夏天的能量渐次地释放了出来。竖纹枫的肢体开始变色,先是树梢,然后朝阳的一侧,或黄或红,稳重而渐进。不似身旁的伙伴白肤枫,只是斑斑点点,叶子还没有红透,便悄然飘零,发出轻轻的叹息,犹如透支早衰的中年人,朝如青丝暮已成雪。
疫情的羁绊令人压抑,好久未能同框的我们终于在几场漏夜秋雨之后一同走到小区。
“啊,太美了!”妻和我都惊呼起来。满街满区,连同楼宇之间的空地和小径都成了调色板,色阶刺激着我们的视神经,染花了视网膜,令我们惊叹、激动和愉悦。杏黄、明黄、娇绿、翠绿、柿红、橘红,乃至各种中间色交错混染,冲击着眼底和心灵,枫的主场戏开幕了。
枫之骄子啊,或悄然飘落,或随风起舞,满天的彩星,风儿不再寥寂;或飘落满地,或挂罥树梢,装点着四周,大地不再单调;或冲墨洇晕,或率性地披红裹黄,撞击着视野,人们不再压抑。那飘落的是瓜熟蒂落,丰收的喜悦,岁月的流丹;那舞动的是色阶的嬗变,心灵的浪漫,生命的轮次。满树的红黄绿斑驳陆离,满地的姹紫嫣红醒目怡神,满世界飞舞的杏黄葱绿扑入眼际。这是看不尽的灿烂,留不够的烁金,拾不完的欢愉。枫叶在尽情地欢唱,在倾心地描绘秋韵图,在霜降前发出最后的呐喊。
走在竖纹枫斑驳厚实的落叶上沙沙作响,看着虽说单薄却也浪漫的白肤枫的红叶,只有一个感觉:殊途同归。
一片枫叶,从春写到了秋,从生命的原点写到了英雄陌路和美人迟暮,总算结束了。“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此景此情,寄与故土,寄与关山万里的亲人。
我喜欢秋枫,多彩、壮美、富足;却又不能忘记单调、朴素、平庸。没有初始,便没有成熟;没有坚持,便没有始终;没有厚积,便没有薄发。树如此,人亦如此,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历程。
本文作者简介:
王志光博士,中文教育学者,曾在加拿大和中国大学教授语言 40 余年。1993 年创办温哥华北京中文学校,为华裔及其他族裔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平台。曾任校长,现任校监。加华笔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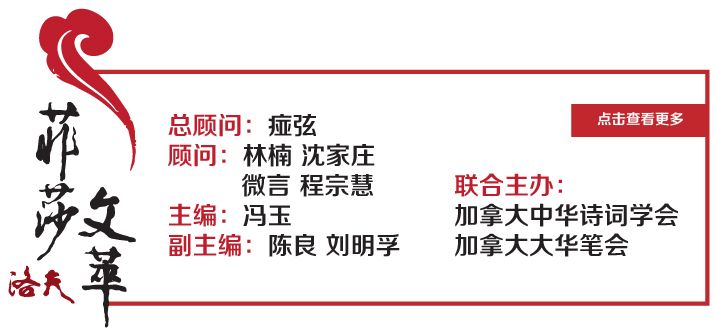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