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的温哥华的夏天十分凉爽,初到温哥华的我,刚刚有了身孕,特别害怕感冒,每次出门总是带一条轻薄的披肩,坐在海边或阴凉地,披肩就派上用场了,而且比一件夹克衫之类的外衣更随心所欲,有时碰到小雨,也可以临时用来遮挡,像阿拉伯妇女那样裹在头上。可没有想到不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那之后的一天,丈夫突然很严肃告诫我,你出门不要戴披肩了,别弄得跟什么人似的!我一愣,但马上领会了他说的“什么人”是指什么人。虽然有点不情愿,但也怕走在外面被人侧目,就暂时放弃了披肩。其实九月以后的温哥华,披肩在户外更是实用。然而,在当时美国遭遇恐怖袭击、全世界都惊魂未定的特定时期,披肩与围披肩的人也令人产生负面联想了。

之后的某一天,我们和一对朋友夫妇去Deep Cove海滨村游玩,玩累了就去当地一家我们熟悉的咖啡馆歇脚聊天。快到跟前时,看到门口坐着六七个中东人,男人都是大胡子,有的头上缠着一圈圈的裹布;一位年老的女性穿着深蓝色罩袍,不过露着面部和脖颈,并不那么严实;另外稍年轻的女性则戴着莎伊拉,一种长方形围巾,松松地裹在头上落在肩部围住。我们一行几人居然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互相看看竟异口同声地低语,别和他们坐在一起,换一家吧。
这件事过去了这么多年,仍记忆犹新。我也曾偶尔在内心里替那天坐在咖啡馆门口的几位中东人感到冤枉,仅仅因为他们的模样和装束,当时我和我的朋友们选择了与他们保持距离,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想一定不仅仅是我们。偏见和成见属于客观存在的心理学现象,是每个人身上固有的东西,而无法从我们人性中剥离出去。在人类社会的生活现场,要做到完全没有成见、不带偏见地对待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某一特殊事件发生后。然而,在对待具体的生命个体时,是否带着偏见的行为,往往会成为人性善恶的的考验。抛开先入为主的社会成见,或许只有天真无邪的孩童才可能具有尚未被社会、政治、种族等等污染的自然善意的人性。

泰戈尔写于1892年的短篇小说《喀布尔人》里的“我的女儿”米妮就是这样一个天真可爱的五岁小姑娘。小说描写了小米妮与走街串巷的小商贩喀布尔人罗赫莫特之间的亲密友谊,这种友情超越了年龄、阶层、社会地位悬殊。罗赫莫特从第一次见到米妮冲他喊“喀布尔人”的那一刻,就对这个完全不同于自己出身阶层的小女孩明显表达出喜爱。当被逮捕的他在反抗和怒骂时,一听到米妮童真的呼喊,就瞬间由暴力转而温和与慈祥,就像发怒的狮子被施了魔法一样即刻驯服了。何以米妮对这个喀布尔人有这么大的魔力?直到十几年后米妮出嫁的那天,谜底终于揭晓。
那天,罗赫莫特恰好从牢里放出来,他带着以往每次跟米妮见面都会给小姑娘的一串葡萄和一小纸包的干果来看米妮。而长大了的米妮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会无拘无束地跟他说笑了。读到这里,我的心也像小说里的父亲一样隐隐作痛了。当米妮的父亲为罗赫莫特带给女儿的小食付钱的时候,喀布尔人拒绝了,说自己不是为了卖东西而来的。。他从自己胸口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上面印着他自己的小女儿的手印,这个小手印让他在远离家乡的时候“仿佛感到有一双温柔的小手,在抚摩着他那被离愁折磨着的心”。读到这里,我的心被震撼了,泪水瞬间模糊了视线。虽然喀布尔人与米妮的父亲“我”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卑贱者内心的父爱绝不逊于上流社会的父亲。“我”正是通过女儿米妮与罗赫莫特的交往,对喀布尔人的态度由怀疑、排斥转化为理解和同情。泰戈尔描写了不分阶级、不分贵贱的父爱,并以这同样的父爱,诠释了人性平等的理念。小说的悲悯情怀,表达了泰戈尔排斥政治因素的和平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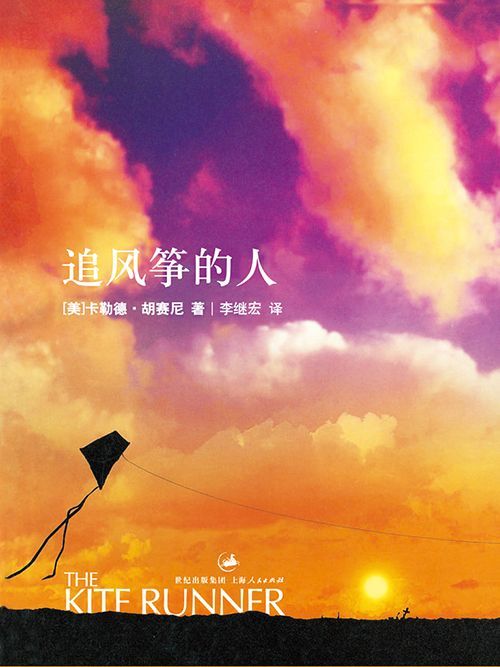
从泰戈尔《喀布尔人》,我又想到当代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作者以深情的笔触和沉痛的反省书写了阿富汗的富家子弟与仆人的儿子之间的感情故事,深刻剖析了人性的背叛与救赎。小说是2005年美国排名第三的畅销书,它以现代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人性和人性的拯救,撼动了全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读者的内心情感。
小说中的“我”阿米尔是喀布尔富商的儿子,和他家的仆人的儿子阿桑是同一个奶妈的胸脯哺育的,从小亲如兄弟,如影随形。阿桑对主人忠心耿耿,任何时候都心甘情愿为阿米尔做出牺牲。阿米尔爸爸欣赏阿桑的正直勇敢,失望于阿米尔的怯懦。阿米尔则妒忌爸爸对阿桑的爱。作者用强烈对比的手法描写了两个性格和行为迥异的孩子。阿桑宁可受辱被强暴,也不肯交出那个代表阿米尔赢得斗风筝冠军的蓝风筝。然而阿米尔目睹阿桑受辱却没有挺身而出,而是逃避。之后因深受良心折磨而无法面对阿桑,却又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过错,反而以更大的错误去掩盖之前的错误。他设计陷害阿桑偷了自己的生日礼物和钱,以便父亲可以解雇阿桑父子。阿桑洞悉一切,却没有说出真相,而是含冤承认偷窃,再次为阿米尔牺牲自己。尽管蒙在鼓里里的爸爸选择原谅阿桑父子,但明了一切的阿桑父子决意离开。而他们的离去,并未给阿米尔带了解脱,他陷入了一生的负罪愧疚的阴影之中。直到成年后在美国定居的某一天,父亲的挚友临终前通知阿米尔去解救阿桑的儿子索拉博,并告知阿桑其实是阿米尔同父异母的兄弟。而此时阿桑已在喀布尔为保护阿米尔家的大房子被塔利班枪杀,索拉博被送进孤儿院,后又被塔利班头目带走,成为一个被性侵的舞童。作家给了阿米尔最后一个救赎自己灵魂的的机会,阿米尔忠于放下了自己的怯懦,冒着生命危险返回喀布尔救出阿桑儿子,并决心像阿桑当年对待自己一样来对待阿桑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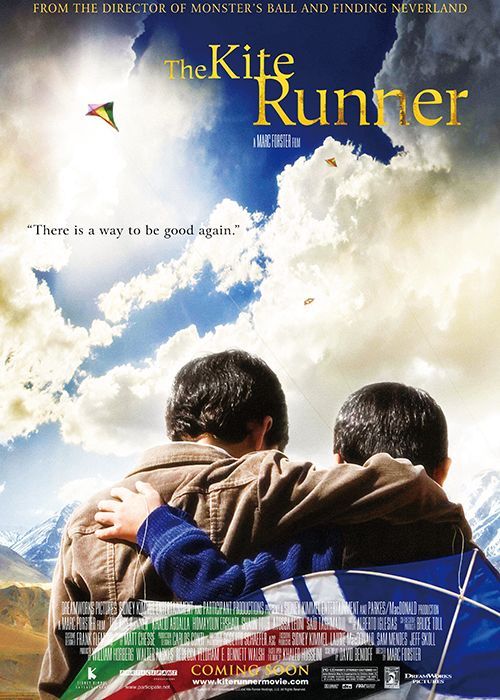
小说中追风筝的男孩哈桑,代表着被凌辱的哈扎拉族人,他身上完美地体现了人类忠诚勇敢、正直无私、勤劳善良的美德。作者饱含深情倾注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笔触,与泰戈尔一样超越了社会、宗教与种族的藩篱,呈现出纯粹的人性的光芒。
回顾中外文学史,无论是从古老中国的诗经开始,还是从西方的荷马史诗开始,文学从来都不曾在人类文明史的沉浮、迂回、前行的旅程中缺席过,那些在枯槁干瘪的、也可能有许多虚假谬误的历史记载之外的伟大的文学,则真实而血肉丰满地记载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里的人类生活的真相和人性的真实。那些被压迫、被侮辱、被奴役、被损害的广大的受苦受难者,也只有在伟大的文学里得以获得拯救。每一个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诗人,他们首先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作品还“卑贱者”以尊严和公正,让世人看到善良美好的人性在被压迫和被侮辱者身上的闪光,让愚蠢的傲慢与偏见自惭形秽。想到这里,我内心有一股潮水般的冲动,忍不住要深深地弯下腰来,向这些具有悲天悯人情怀和深刻洞悉人性隐秘的伟大作家极其伟大作品鞠躬!

在阿富汗政权更迭的风云变幻之际,当地人民陷入被塔利班重新统治的前景未卜的恐惧,喀布尔国际机场惊现人们疯狂逃离的混乱与悲剧中,喀布尔,成为国际新闻与政论节目中高频率出现的词语中最令人揪心的一个。不知怎么我开始厌倦那些喋喋不休的政论,而在泰戈尔和胡赛尼的悲悯情怀里静静地走近喀布尔人,甚至想象着某一天,新来的邻居正是从喀布尔逃出的难民,而且是长着很像中国人脸的哈扎拉人。

© 加拿大高度传媒集团版权所有。若无授权,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